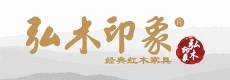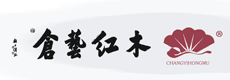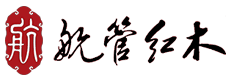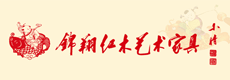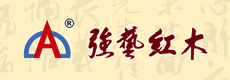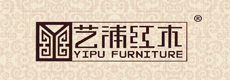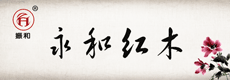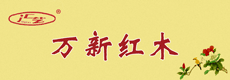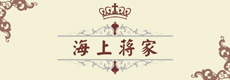犀皮中的“工”与“美”——(下)
犀皮中的“工”与“美”——(下)
犀皮中的“工”与“美”
2017-07-14 作者:张天星 浏览:2292 来源:中国红木艺术家具网
摘要
3 犀皮中之“美”的研究
在《中国艺术家具的工艺观》一文中,笔者曾论及,中国艺术家具之美是“工美相融”的美,犀皮作为其中之一员,自然不例外。在犀皮中,其内之“美”离不开“知”【3】,亦离不开“行”【3】,“知”赋予美以“内容”,使其与基于“形体感受”【4】的美有所别,而“行”则是美参与“实践活动”的推动者(此过程使得美脱离“纯粹美”【4】的范畴)。
3.1 “美”与“知”
对于美中之“知”而言,其是犀皮中的“认识活动”,此活动包括两部分内容,即对“美”之定位的“知”与对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间之关系的“知”,在“定位”方面,犀皮之美隶属“文化—心理”层面之美,首先,犀皮之美离不开递承,递承在于中国之造物理念的延续,即“天人合一”之思想在犀皮之美中的体现,在犀皮中,其内之美的最终显现是综合因素相融的结果,预想实现最终之美,既离不开主观群体之所想的引导,亦舍不掉实现方式(即打捻)与工具(即手、薄竹条、磨石与碳粉等)的助益,这“心物相融”之理念即为“天人合一”在犀皮之美中的流露。其次,犀皮离不开创新,创新是当代之主观群体突破前人的关键,犀皮之创新源于“实现方式”与“手段”的改变,其与延续前人之“技”的创新有着本质之别(本质性的创新源于实现方式与手段的突破,否则依然隶属“表象”之创新的范畴)
在犀皮中,“打捻”即为突破前人之实现方式与手段的关键,其之助益,才使得犀皮之美既不同于以手“起花”的“磨显”之填漆,亦与借刀成纹的“镂嵌”之“填漆”有所区别。最后,犀皮离不开内容的融入,其中的内容源于主观群体基于“文化—心理”层面的一种“联想”,即主观群体可从犀皮的“纹”(诸如片云、圆滑与松鳞)与“色”(色漆的相间与杂糅)中感知“中国设计”之“根”,如对工艺观、方法论与设计方法的理解与顿悟,均属“有根”之例,可见,犀皮之美中的“内容”并非是主观群体对“形式”的“直接感受”或“联想”。通过上述之言可知,犀皮中之“美”的定位既与“生理”层面之美不可同论,又与“生理—心理”层面之美判然有别。
除了“定位”,美中还包含对“认识活动”与“实践活动”之“关系”的“知”,认识活动是实现主观群体之所想的过程,而实践活动则是落实主观群体之审美的过程,前者隶属构想之阶段,后者则需在具体操作中完成,故在将思想与审美进行可视化的过程中,必会出现冲突之状况,此时,便需主观群体对两者之关系进行探析,该种探知便是其利用“所知”将“对立”的矛盾转换为“互补”或“互融”的过程。在犀皮之中,主观群体预想实现基于“文化—心理”层面之美,必须解决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中的矛盾,对于犀皮之美的“认识活动”而言,其既包括对实现“肌理式”美之“方式”与“手段”的构想,又不排除对工具之材料与式样的选择。在实现的方式与手段方面,主观群体采用先“打捻”,再刷涂色漆,而后在磨显成纹的思路予以实现犀皮的“肌理式”美,可见,犀皮之美的实现方式与手段与前人之“技”截然不同,故无法借助已有之工具成就这“殊相化”【5】之美,因此,在此思路中,实现“方式”和“手段”与已存的“工具”间出现了矛盾之势;对于犀皮之美的“实践活动”而言,其包括两部分内容,一为针对“工具”的实践活动,二为具体过程的实践活动(即将制作过程),在“工具”的实践活动方面,其是主观群体之思想与实现方式和手段顺利践行的重要因素,在犀皮中,对于“工具”的实践活动意指“薄竹条”制作过程,通过前述的内容可知,打捻之工具既可以“手”完成,亦可借“薄竹条”实现,但为了达到“纹”与“色”的婉转流畅,薄竹条需精心设计,即开出不规则的齿状,以满足打捻之需要,这从设计到不规则之齿状的诞生,便为针对“工具”的实践活动,此实践活动是化解实现方式与已有工具(意指“其他工艺”中所用的工具)之矛盾的核心力量。在“制作过程”之实践活动方面,其是践行矛盾转化的具体过程,即主观群体利用所选之实现方式与工具实现犀皮之美的活动,可见,此种实践活动不仅可化解主观群体之所想与实现方式间的矛盾,亦可将前两者(即主观群体的思想与实现方式)与工具间的对立转化为互融。通过上述之论可知,对于“认识活动”与“实践活动”之“关系”的“知”,即为将矛盾中的“对立”转化为“互融”的过程。
综上可见,犀皮之美中的“知”既非是隶属“形而上”之范畴的“知”,也非是只局限于“形而下”之阵营的“知”,其是既带“形而上”,又含“形而下”之“形而中”【6】的“知”。
3.2 “美”与“行”
在犀皮的美中,其内之“行”【3】,即“制作过程”【7】、“实现过程”或“实践过程”,在该过程中,涉及三部分内容,即主观群体之思想与审美的实现过程、方式与手段的实现过程与所用工具的制作过程。对于主观群体之思想与审美的实现过程而言,其是“物化”的体现,“物化”即将主观群体之思想、行为与属性转化为物之行为与属性。在犀皮中,其内之美亦需历经“物化”之过程,即利用工具将主观群体对犀皮的“设计过程”与实现方式(即“打捻”)在工具之助益下进行制作的过程,此中的“工具”便为“物化”中的“物”,通过上述的内容阐述可知,犀皮的制作工具为“手”或“薄竹片”,其之采用,并非反对机械,崇拜手工,而是主观群体实现原创的需求,由此可见,该种“行”(即主观群体之思想与审美的实现过程)并非是“物”占统治地位的“行”。
对于方式与手段而言,其之实现过程体现于“矛盾”的“解决”之中,矛盾源于“新”与“旧”的碰撞,预想使得“新事物”出现有别于“旧事物”的本质性标志,便需具有“突破性”之“思维方式”的配合与参与,即“新”的实现方式与手段的诞生,犀皮作为有别于前人之作的新事物之一,其亦不例。在犀皮之中,“打捻”即为突破性的实现方式与手段,其之存在,不仅化解了“物化”过程中的矛盾,亦将“人化”过程中的矛盾从“对立”转化为“互融”,在“物化”过程中,“打捻”的存在避免了主观群体之“设计思想”的属性完全转化为所用之“工具”的属性,在此过程中,设计思想与工具即为矛盾的双方,若实现方式与手段(即“技”)采用得当,便会令两者之,矛盾转向“互补”与“互融”,如以“手”或者“薄竹条”实现“起花”,即为解决矛盾的见证,若所用之“技”(即实现方式与手段)不当,便会使两者之矛盾趋向“对立”,由此可见,“打捻”虽为实现犀皮之“美”的方式与手段,其却需在实践活动(即“物化”)中完成;对于“人化”而言,其与“物化”相同,其内亦有矛盾的存在,在犀皮之中,其内之“人化”是为“载体”与“工具”赋予“美”的过程,此中的“物”(既“载体”与“工具”)与“美”即为矛盾的双方,预想避免主观群体之思想过于 “个性化”,致使出现“失度”与“失宜”之过,实现方式与手段的干预实为必要之举。“打捻”作为犀皮的实现方式与手段,即为令“载体”、“工具”与“设计思想”间之矛盾摆脱“物”需追随“设计”的倾向。综上可知,无论是“物化”过程,还是“人化”过程,均为成就“美”之实现方式与手段的实现过程。
对于工具而言,其之实现过程包括两种情况,一为“自体”【4】的实现过程,二为落实解决方式的实现过程,之于前者而言,其是实现有别于前人之美的物质性基础,在犀皮之中,“自体”的实现过程意指 “薄竹片”的制作过程,为了达到所显之“纹”如行云流水般自然婉转,此工具需制成“不规则”的“齿状”以为“起花”之用,可见,该工具既有别于前人之所用,诸如以破螺钿沙、石黄、石绿、石青与朱砂等“起花”之“具”,亦与“有限性”与“规则性”之工具差异非同,此种带有不规则之齿状的薄竹条是实现殊相化之美的重要因素,可见,此种“自体式”的实现过程与美相辅相成;之于后者而言,其是实现方式得以具象化的物质性基础,在犀皮之中,打捻作为实现的方式与手段,其虽可通过思维之突破将矛盾的对立转化为互融,但若无“具体物质”(即工具)的配合,其恐难成为可视化的现实,在犀皮中,打捻实现其之美的手段与方式,其需“手”或“薄竹片”的参与,“手”作为“工具”之一,其可使“打捻”获得“灵活”、“自由”与“多样”之性,诸如片云、圆花与松鳞等纹,即为见证之例。除了“手”,在犀皮中,还可借“薄竹片”代之,若操作得当,其依然可令“打捻”有回转自然之感。可见,无论是工具之“自体”的实现过程,还是落实解决方式的实现过程,均与美分割不得。
综上可知,犀皮的美无法离开“行”而单独存在,无论是主观群体的“设计思想”,还是解决矛盾的实现方式与手段,抑或是落实前两者的工具,均无法脱离实践过程而“自体”运转。
4 结语
对于犀皮而言,其作为中国文化的承载者之一,故无论是其内之“工”,还是其内之“美”,均离不开中国之造物理念的渗入,在“工”之方面,其虽为“制造过程”,但却离不开“技”、“具”与“艺”的配合,“技”作为实现方式与手段,其是突破前人达到创新的关键;“具”作为犀皮中的物质性因素,其既不同于实现一般性之“手工劳动”的“工具”,亦与工业化下之“机械”区别甚大,犀皮中的“工具”具有“灵活”、“自由”与“多样”之特点;“艺”作为犀皮中的精神性因素,其使的“工”与“设计过程”(即“美”)互融。在“美”之方面,其包括三方面的内容,即定位、知与行,之于“定位”而言,犀皮之美既不同于主观群体对美的初步反应(即基于“生理”层面之美),亦与基于“形体感受”的“直接式”联想有所区别(即基于“生理—心理”层面的美),其是基于“文化—心理”层面之美的案例;之于“知”而言,其内既包括“认识活动”的“知”,亦包括“实践活动”的“知”,可见,“知”令犀皮的美脱离“纯粹美”之范畴;之于“行”而言,其是成就美的“实践过程”,在犀皮中,预想实现其美,既离不开“设计思想”的指导,又需实现方式与手段的突破,还需“工具”的配合,无论是设计思想,还是手段与方式,抑或是所用之工具,其所含之美均需在“实践过程”(即“性”)中完成,可见,美与行无法分割。综上可知,无论是犀皮之“工”,还是犀皮之“美”,均非各自独立的“制作过程”与 “设计过程”。
|
术语解析 |
|
1 菠萝漆: 菠萝漆因花纹形态类似菠萝削皮后的肌理而得名,最初,其名为“破螺漆”,在此工艺中,主观群体需以“破碎”的“螺钿沙”以实现“起花”的过程,而后在套髹色漆,待漆干后,再磨显其纹,可见,“破螺漆”之名与“起花”所用之“物”不无关系。随着时间的发展,人们开始以“石黄”、“石绿”、“石青”以及“朱砂”完成“起花”,“破螺漆”也渐变为“菠萝漆”。
|
|
2 虎皮漆:虎皮漆即“波罗漆”,其名与唐朝的云南南诏有关,在当时,人们将“虎”称之为“波罗”,故得“虎皮漆”之名。 |
|
3 波罗漆:又名“犀皮漆”、“虎皮漆”与“桦木漆”,其是南方匠师对犀皮漆之称呼。“波罗漆”与“菠萝漆”如此接近,必有联系之处,也许“菠萝漆”是民间效仿“犀皮”的一种做法,后因其与犀皮的“起花”之法类似,故近现代之匠师以“波罗漆”唤之。 |
|
4 片云、圆花与松鳞:三种均为犀皮之花纹。 5 磨显:“磨显”是填漆的做法之一,其是以稠漆堆出花纹之轮廓,而后在轮廓内外填充色漆直至通体平齐,待荫干后,在进行打磨,以显其纹。 |
|
6 渐灭:渐灭是髹饰工艺在磨显纹饰时所犯之过失,即磨的“太过”所致。 |
|
7 搓迹:搓迹也为漆之打磨中出现的过失,由于磨的“过急”,或所用之磨具中含有“杂质”所为。 |
|
8 蔽隐:其亦为髹饰工艺在磨显纹饰时的过错,由于磨之力度欠佳致使隐蔽在漆面之下。 |
|
9 镂嵌;其与“磨显”相同,均为填漆的做法之一,“镂嵌”是在漆地上镂刻花纹,而后将色漆填如其中,待荫干之后,进行打磨即可。 |

扫一扫有惊喜!